编者按:
近日,“澎湃·镜相”第二届非虚构写作大赛获奖名单揭晓。本届大赛以“渺小与苍莽”为主题,特设奖金池33万元,旨在挖掘关照现实、书写时代与个体,记录磅礴与幽微的优秀佳作。大赛由澎湃新闻主办,七猫中文网、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联合主办,邀请来自学术、创作、出版、影视界的多方代表共同参与评审,从选题、信息和文本等多维度考量,最终评选出12篇极具潜力的非虚构作品,并将继续推动出版和影视改编等多种形式的内容开发。
《玩乐时间:“六合彩”中的心灵与社会》(作者:欧椋)是一份关于昔日地下六合彩的田野调研,作者剖析了“玩乐”中的社会学逻辑,以及荒诞背后,一代人的精神境遇。该文获此次大赛“澎湃七猫特别奖”,以下内容为获奖作品节选,“镜相”栏目独家首发,如需转载,请至“湃客工坊”微信后台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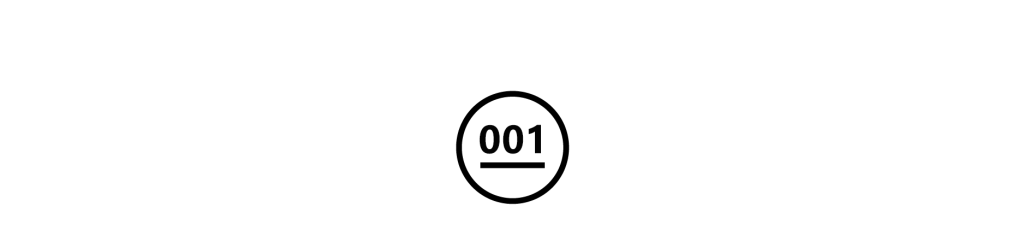
特码之夜
张丽的家里正人头攒动。有人刚从室外走进来,有人已经下好了码交了钱,正在走出去。新来的人,尚未沾染上温热油腥的人气,顺着人与人的缝隙逆流而上。张丽看着他们黑鱼一样钻进自己的卧室,一张张红扑扑的脸颊偶尔钻出人群的水面,浮出来透口气。有人因为太激动,已经坐在了她的床沿上。这些人把房里的书桌团团围住,卷心菜一样包裹着最中心的人——张丽的外婆手里正捏着笔,手指翻飞按着计算器按钮,机械的女声忙不迭叫着“二三四五-加-四八零,加…”很快又被电话打断,叮铃铃,像一只顶端尖锐,羽翼做尾巴的箭,刺向嘈杂的空气,却只是虚晃一枪,没有飞出去多远。电话很快被接起来,外婆翻出一本卷了边的本子,刷刷记下一串数字。周遭的讨论并未降低音量,数字从人嘴里钻出来,裹上香烟,飘到书架上、床铺上、藏在天花板电灯内壁里的苍蝇上,张丽开始佩服外婆强大的抗干扰能力。
五分钟前张丽刚挨了一巴掌,她忘记了今天是开奖的日子。当她在另一个房间里看电视的时候,电话响起,她接起电话,对面说:“梅芳姐,我今天下3号。” 张丽纳罕,“喂?”这时她又从电话里听到了外婆的声音。张丽还未放下听筒,外婆已经从另一个房里冲过来,扯住张丽头发劈头扇了她一巴掌。
从那以后,她才知道她们家有一根电话线、两台电话。一台电话在卧室,里面放了一张大床和两张小床,能睡下三个人:张丽、张丽的哥哥和张丽的外婆梅芳;另一台,放在曾经的书房,张丽曾经睡在那里,但自从2003年梅芳开始给六合彩写单之后,这间房已经被改造成了下码专用的场所,于是书架上的郑渊洁、杨红樱等童书被束之高阁,而下码用的码经、小报、账簿铺了一桌。人们涌入之后会翻阅这些码报,然后展开讨论。所有的一切,都被童书封面上咧着嘴的舒克和贝塔用两双鼠眼注视着。
每个开奖的夜晚,书桌上的电话就会连串地响起来,一通接一通,梅芳通常会在三秒之内接起来。而这次,张丽恰好在卧室里听到了电话铃声,她没有思考便接起来。梅芳在书房听见张丽的声音,认定她在捣乱,气势汹汹地赶过来,先甩了一巴掌,再接起了电话。很快,张丽的哭声、码民们在另一个房间里的争辩声,通通被她抛之脑后了。她此刻心里唯一的任务是——记下电话那头要下注的数字,连着人名写下来,等到开奖之后,她会核对好一切信息,再分别回拨过去。她的心狂跳着,有无声的鼓点催促着她。
在开奖的晚上,来电话的时间点很重要,下码的人和报开奖号的人都会打这个电话,八点前接起来的电话,周围众人只是漫不经心地听,如果有生肖、数字从听筒里泄露出来,他们会和自己的对照一下,笃定的人会暗笑,“又是个冤大头。”茫然的人会开始焦虑,“要不要再加一个号?”
但是八点半之后,所有人的神经就会开始紧绷,一点风吹草动,就会让坐着的人站起来,站着的人走动起来,靠近梅芳的人会将头前倾,站在门口的人会侧身随时准备传话,所有人都像士兵一样随时准备着,梅芳则像将军,一只手横在空中,随时可能比出数字发号施令。
每周二、周四、周六的八点到九点,梅芳的家人会自觉地不拨打任何电话,因为随时可能会有人打电话给她,询问或者透露消息以及通知特码。八点钟时,码民德昌因为梅芳的号码一直占线,索性出门来到现场,站在梅芳的黑漆方桌旁,捧着半张纸,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报。梅芳运笔飞快,仿佛在完成听写作业。
六合彩最基础的下码机制很简单,每周二、四、六开奖,在1-49之中开出6个基本号码,以及一个特殊号码,称为“特码”。码民只要买中了特码,就会得到1:40的赔付。几个月以前德昌中过一次,但不幸只下注了十块,赢来的四百元又在之后全部压了上去。现在他已经完成了开奖前全部的任务,只需要坐在凳子上等待。码民们的手指无处放置,便反复摩挲着自己的玻璃茶杯,翻来覆去地折叠、抖动、拍打手中的码报;那些不幸空手而来的人,双手则徘徊在着额头眉骨的一点点轮廓上。
八点半,梅芳的电话响了一下,他看着梅芳立刻接起来,心跳得很快。但在八点四十五之前的电话都不会让他特别激动,在这以前,他还可以随时加码、更改自己下的数字,但一旦过了八点四十五,再打来的电话就可能会开始报特码了。一个数字,中与不中,只在一念之间。从下午开始念叨的几个无意义的数字环绕着他。他继续等。
电话响了,梅芳一把抓起电话,众人疲惫之余也露出嗔怪表情,竟也有人不想立刻知道。但无一例外,所有人都一齐盯着猩红色电话听筒,胸腔鼓胀,像牛一样用鼻孔微微喷气。电话那头传来模糊的声音,梅芳点头,手中的红色斗牛旗也随着摆动。坐着的人站了起来,很快又因为挡住别人视线被拨走。梅芳伸手朝身后比了一个数字,立刻就有志愿军一样的人大声念出她的手势——“二十五”。立刻有人双手拍一下,又摊开,来证明这个数字至少曾短暂地在他大脑停留过。
张丽的房间立刻沸腾了,有人要凑上书桌前去对账,有人意犹未尽地走出去,有人不敢相信,反复追问确认着。屋内盛满了嗡嗡的人声,每个人嘴里都衔着几个数字,对着彼此念出来,没中的人立刻结成了一个同盟。张丽想起考完数学月考时,聚在走廊上对答案的傍晚。
在路上遇到的随机数字可能不会让人额外留意,甚至不构成意义。但在开奖的夜晚,数字是一种味道,从码庄手中的电话听筒里散发出来,沿着门廊流窜到客厅,最后跑出去,混合了门前的香烟卷、杉树皮、油菜花的气息,从巷尾飘到另一头,人们闻了去,就知道一个夜晚的结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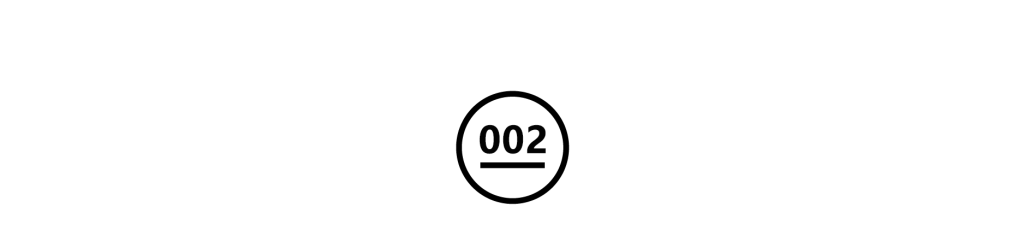
阐释的游戏
从阅读码报、在生肖、颜色与数字之间流连、揣测,到讨论、做决定,“买码”有它的乐趣。其中很大一部分快乐来自于解读。
中国文化有深远的“阐释的历史”,禅师说的话、统治者的话、书籍中的话,通通都需要阐释。汉语充斥着典故与玄机,是一门适合把玩的语言。从参破玄机、揣测上意,再到生活中的解谜游戏,中国人酷爱阐释性行为,这些对解谜的推崇在六合彩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每个开奖的夜晚,人们聚集一堂,在码庄的家里讨论自己白天所见的神秘数字,阅读码报的参悟,梦境中的玄机。
首先是阐释权威。用于提供玄机线索的码报、码经以报纸、书籍的形式呈现,因而形成一种知识上的权威,让人产生文化上的安全感和信任感。此外,在谣言中,《天线宝宝》和《天天美食》等节目与特码玄机相关。这些由官方电视台播放的节目更是让人对六合彩的权威深信不疑。
六合彩的风靡,也以当时电视在中国乡镇的推广为背景。对当时只熟悉电报、广播、报纸的人们来说,电视是一种全新的视觉力量,说服人、混淆人、让人坚定地认为自己的生活与电视中所呈现的景象有着深切的联系。不然的话,为什么人能够观看到屏幕里的一切?我为什么会恰好看到这一幕?它暗示了我生活中的什么?
视觉的联系是一种具身的联系,眼球的亲近让人们混淆现实与电视里的一切,认为它不过是一扇窥见他人隐私的窗——既然都是眼中所见,那又有何区别?只是这扇窗不通向邻里和街区,而是朝向一种权威、决定性的“上面的”力量。于是,热爱从电视中寻找线索的码民们几乎有了一种宗教体验,认为既然自己被安排看见这些情景,必定是玄机之手在暗中发力,将自己的背推了一把。
对电视上随机的细节赋予意义,也是小镇居民们应对这一新兴媒介带来的认知冲突的方式,他们在面对电视这一媒介时,并不能完全消化它。对电视的观看一方面反映出新旧媒介冲突期,人们在媒介使用上的认知冲突;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的现实世界已经被六合彩所渗透,因此,在这样一种滤镜之下,电视作为一种连接了日常和官方的媒介,更加成为人们投射幻想的对象。
第二种阐释的倾向,关乎对女性身体的神秘化。在地下流通的特码刊物中,有一种《白小姐特刊》特别受欢迎,其中每一页都会有一个赤裸的女人,胸部等私密部位被五角星、圆形等色块遮住,仿佛悬浮在她们身上,每一个色块上都有一个数字,透露着特码相关的讯息,让码民们可以正当地、光明正大地注视。这里的遮挡充满了矛盾性:遮蔽住女性身体的奥秘,但却透露出特码的玄机;有性的禁忌,但也泄密欲说还休的线索,邀请观看者解读。
在这里,女性的身体充当了谜团的载体,同时也成为了另一层解密的对象。对女性身体的神秘化倾向由来已久,许多文学艺术作品都将女性描绘为不可知的、神秘的、等待被男性解读和驯服的对象。这种描述以性为底色,一方面使性本身变得高深莫测,也反过来将女性塑造成通往神秘的使者,使她成为信息、谜题的载体,同时也是等待被解读、被揭晓的谜题。因此,她们身体的裸露既是一种泄密的过程,同时也通过展现“神秘”,而加重了“神秘”这个存在本身的光晕,显得更加面目模糊,迷雾重重。
女性的身体烘托了解谜的氛围,在神秘化的同时也让猜测玄机的游戏中充满了挑逗。神秘化的女性身体,既是谜面,也是谜底。由此,码民们被暗示了一种解谜的逻辑:当她展示出的谜题被破解后,谜团的浓雾散去,露出她的赤裸身体,这就是对解谜者的奖励。解谜者能通过解读和揭秘来让特码显形,同时也让面前被遮挡的女性身体完全赤裸。此处,玄机与女性身体合二为一,揭秘如同宽衣,让解读特码变成了一种征服与挑逗。
这种神秘通常体现为对女性身体的局部化处理,而忽视她作为人的整体性。通过分割、遮蔽和突出局部,身体被划分成不同的区域和部分,根据眼睛的观看方式、审美的喜好,来呈现身体。对女性身体的“切割式”呈现,就如同透露玄机的过程,用数字、打油诗埋下伏笔,设置悬念,等待观看者解码。
因此,阅读这类特码报刊是一种对身体和心灵的唤起,解密的过程伴随着对女性身体的窥探和意淫。对神秘的谜的解读和对性的联想遵循了同一个思路,鲁迅所说的那句“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在此处,有了双重的解释力。
第三种阐释在于对符号本身的解读。码民们在阅读码报时,并不一定会遵循六合彩的逻辑,而是在其中开辟出了新的阐释空间,暗藏了对个人身份的演绎。在2005年前后,丁丁正在上小学。因为父母工作太忙,她妈妈会委托自己朋友的母亲照看她。这位六旬老人在和丁丁相处熟络之后,突然有一天,拿出一个皱巴巴的软皮本子,指着上面的一个图形,问她:“姑娘,这个字,你认识吗?” 小学二年级的丁丁不太确定这是不是一个汉字,只能点头,又摇头。老太太遂又翻了一页,指着散落各处的笔画、图形,问丁丁:“那这个呢?”
在六合彩的码报上,有字谜、玄机图种种,用来给码民一些提示与线索,而对于不识字的人来说,文字并不具有实际的意义。因此,有些码民会拜托识字的人给自己念出码报上的玄机诗,在心中记下之后,再在本子上临摹出偏旁部首。面对纸上经过一个个比划拼凑出来的文字, 小学二年级的丁丁也并不能完全确定眼前这幅图形是否真的是一个字。于是过了几天,丁丁带来了厚厚的新华字典,对照着老太太划下的偏旁部首进行查阅。有些笔划的组合并不能构成汉字,她便排除,有些组合她能在字典上看见,于是便认出来,这是一个字!老太太便对照着再抄写一遍这些“真的”字,第二天拿去码庄处让人看看,和生肖、数字、波段有无联系。尽管在两人眼中,这些横竖撇捺的符号并不构成实际的意思,但识别和破译能够让原本毫无意义的“符号”变成“字”,就这样,丁丁间接地参与到这个盛大的解谜游戏中。老太太期待背字典的小女孩每次的来访,两人一起合作,让陌生的符号变成有效的文字,再从中参透玄机。

赌徒的心事
民族志《蝶变》记录了香港的赌客们在澳门赌场豪掷千金的故事。在经历了一系列过山车般起伏的一夜之后,赌客们从富丽堂皇的赌场出来,坐上回香港的船,心中空茫一片,有“风吹鸡蛋壳”之感。
赌客们说:“输了还要搭一个小时的船,真是惨,虽然是光天化日,却觉得整个天空都是灰色的,脑袋一片空白。回到香港,望着广东道上的楼,一片空虚。”
“去梳打埠(澳门)回程时,有风吹鸡蛋壳之感。即使赢钱,坐回程船时都会有这种感觉,有时会不知不觉想起家人,想起你的那一半,此刻感觉很空虚。不知有没有人和我一样。”
“风吹鸡蛋壳,财去人安乐”是一句粤语区常见的谚语,在《唐伯虎点秋香》中,周星驰饰演的唐伯虎也曾用这句话来调侃赌博输尽家产的祝枝山。当鸡蛋碎掉之后,蛋黄蛋清皆已不在,风拂过一层薄薄脆脆的鸡蛋壳,人竟不知从何处生出一种坦然来,再也不需要担心失去财富,只剩空壳在风中摇摇欲坠,人生如此清脆。
这种空荡荡的心情在六合彩的赌客们心中也非常普遍。原先人尚有财富,是一颗有蛋黄、蛋清的鸡蛋,无法被撼动,此时竟不觉有风拂过。而在输钱之后的那一瞬间,人会感觉自己从社会土壤中被连根拔起,积蓄不再,世俗生活里更大的游戏——赚钱,在这一刻也不知道是否还有意义。在空空荡荡之中,规则、社会期待被先搁置一旁,赌博中的刺激已经退潮,人步入自然之中,微风竟很温柔,自然给的触感在此刻重新回到人的身上,自觉拔地而起,如蛋壳般轻盈,也如蛋壳般孤零空落。
而六合彩的赌客们的落寞离场,则没有那么具有电影感,他们只是混杂在人群之中徐徐离开码庄的家。没有码头汽笛声,没有海风拂面吹醒鼓胀了一整晚的头脑。
梅芳说,在六合彩的世界里,下码的人当中,输家常有,赢家几乎没有。而输家之中,也有不同的类型和层次。下码人的性格、年龄、性别、家庭、受教育背景、下码年限、频率各异,因此对成为输家这件事情,大家的接受方式皆有不同。有的跳楼;有的突然一言不发地消失在妻女的生活里,又在几年后的某一天若无其事地回到家中;有的从此不再赌博;有的生出了惯性。
马小天是张丽的同学,他爸爸在当码庄时,曾经在一个晚上吃单时,不幸“吃中了”特码,一个晚上需要赔付十二万。他买断了自己在银行的工作,换来一笔钱,才得以赔给码民。失去了银行稳定的工作之后,他试图证明自己,不断地从事工程开发、商家代理等等活计。等到他的生意终于有了起色时,他取出了还没来得及还给债主的钱,又一次在老虎机里输个精光。
不仅是码庄,就连身处其中的码民们到后来也发现,自己在六合彩中的投入与付出不成正比。明知会输钱,明知这是一场注定要输的游戏时,为什么人们依旧不顾一切地投入其中?
一部分答案隐藏在六合彩自身之中。在这个被新开辟出的自由空间里,风险与选择以一种游戏的方式呈现在赌客们眼前。当现金从码民手中交给码庄手里时,名字被转化成了账本上的字,钱被转化成数字的形式,同人名一起在纸上被符号化了。经过这一轮转化之后,输钱的实感被弱化了。没有回执、没有短信通知,没有一样实物会提醒你钱的流逝,钱只是不见了,并没有换来些什么。开奖的时刻距离登记姓名和金额通常已经过了几个小时,经过开奖的仪式,似乎几个小时前的交付已然距离自己十分遥远。
在这个信任游戏中,赊欠是常见的经济关系。在六合彩上投注的钱,会在后期成为债务,其中的关联性因此被淡化了。因此在下码的过程中,码民们几乎难以感觉到金钱流失的实感。等到最后盘点债务时,人们在潜意识里也不愿意将这份债务归因于六合彩。码民们借此使自己从债务中脱离出来,没人会去责怪自己的分析失误导致了数钱。随着债务被后置,开奖后没有下中特码的挫败感和愧疚感也被后置了。在这个赌博游戏的机制里,没有表面的惩罚,没下中特码所损失的金钱会在几天后才真正失去,码民们没有“输家”这一概念,码民们不觉得自己在“输”,他们只会觉得自己不够幸运。等到开奖之后的一段时间,码民们陆续向码庄支付欠款,这时始作俑者六合彩在这段债务关系里已经隐身了。
金钱的流失似乎捉不到真凶。从下码到金钱流失的这条线被拉得越长,码民们就越难以意识到自己将多少钱花在了六合彩上。人们记得债务,但忘了债务的原因。六合彩通过一种中介化,符号化,也实现了责任的转移,由此,金钱的价值也被悬置了。
地下六合彩丰富的下注形式与组合也放大了游戏感,也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似乎人在其中尤为可控。即使最后没有压中特码,赌客会认为自己只是没有做出“最好的选择”,同时叹惋自己曾如何与特码擦肩而过。这种“差一点”的感觉,虽然可惜,却给人一种站在悬崖边、车流边的感受——与某种无限靠近的命运擦身而过,令人心跳骤快,兴奋又痛苦。当赌民们在房间踱步,踩在马赛克铺的砖上时,每走一步都有踏空之感。
游戏感同时伪装了代价,遮蔽了负罪感和耻感。在下码时,人只是参与一场毫无道德风险的游戏,几乎忘记了“合法/非法”的判断。又因为“热闹的”集体性参与,码民们轻易地躲在人群里,让群体的议论声、欢呼声盖过了个体的责任。当码庄被抓时,他们所感到的不是后悔,而是“人人都下码,为什么只抓我?”的愤恨。
最终这项游戏也影响了这些玩家们对真实人生的观感,影响了对时间的感知,比如人生不再是一岁一岁的年纪增长,而是一轮又一轮的重新开始。这造成了他们的冒险家心态,只要有一点点本金在手,只要人在活着,总是有逆风翻盘的机会,因为新一轮的赌局已经开始了。
与此同时,生活中真正的选择,则被搁置了。显然那些磨人的、琐碎的、起毛边的人生选择,不如六合彩世界的选择来得有趣、反馈及时。在真实人生中,造成的关系的损失则被认为是不重要的,因为家庭的破裂和情感的衰退,都只不过是一期开奖没中的夜晚,让人低落那一阵,生活总是可以继续。误解与错觉,把人生的失去与赌博中的失败划等号,将情感理解为赌资,所以失去时并无实感,因为已经在六合彩的世界中排练过多时了。
甚至有学者用六合彩来解释千禧年后的用工荒现象,邓燕华的洋村研究表明,到了2010年,珠三角缺工的人数已从当年的15万激增到了200万。比起背井离乡去城市打工,留在家乡下注六合彩成为了一个更具有诱惑力的选择。
学者黄斌欢在对广西南镇进行田野调查时指出,在文化生活匮乏的南镇,聚众赌博非常流行,人们经常在山上搭棚,昼夜赌博。在2004年以后,六合彩在南镇风靡。依靠手机,外出广东的打工者和广西留守者之间形成了一个六合彩买卖的循环圈:人们在广东打工赚钱,在广西老家报单。
一方面,六合彩搁置了金钱、道德、人生选择和社会身份,让赌民们“进入了一种悬置生命的状态”;另一方面,它又在重新塑造着自己的结构。阅读码报-下注-开奖-获得奖励,六合彩有自己的仪式和流程。即使输钱,也是赌博机制中的“奖励”,只是奖励的受益对象并非码民,而是六合彩自身。人们通过解读玄机,进入并在某种程度上认可了六合彩的逻辑;而输钱,只是对于码民的一次鞭策,反而加重了他继续跃身于这个赌博游戏的动力。可以说,下注是过程,也是目的,而赌博的结果,只是赌博体验的延续。
倘若我们把下码的房间当作是一个斗兽场,人们苦思冥想后分析出的数字与生肖,就构成了他们的人格代理。人们持续地进行着人格的自我表达,只不过是以符号的形式。以什么样的方式解读玄机?对一个数字下注多少?赢钱之后如何安置?输钱之后如何对待?人们的知识、胆量、勇气、魄力、力量,人生中的价值排序,都清晰地以六合彩为媒介,在众人面前展现得淋漓尽致。开奖的夜晚就成了人们借符号而展开的搏斗——猜中了特码的人,在智力和勇气上都是胜者。在方桌和黑漆木椅搭建成的斗兽场中,鲜血借金钱之身流了一地。
同时,六合彩本身也成为了一门语言,所有人在讨论“波”、“吃号”、“单”与“双”时,默认彼此都完全懂得这些术语。它构成人们生活的背景,一种共通的话题。居民们通过讨论六合彩来沟通。它替代“吃饭了没”成为一句问候,伴随着香烟、自家田里的小葱一起被送到对方手中,再被接下,或别在耳后,或剁碎之后咽下。它所兜售的暴富神话,像是一个所有人都听过的寓言。六合彩的逻辑——只要下中了特码,就会实现暴富,同童话中的道德警示“诚实是美德”、“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等箴言一样,被所有人潜移默化地接受了。
另一部分答案,隐藏在关于掌控感的悖论中。矛盾性的一部分源于人认为自己能够控制:下哪个号?下多少?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范围内。赌民们认为玄机早已定好,能通过各种小报、线索、谜语推测出来,并不是一个无序的随机事件。比起更大的政治经济背景中的不可控,在六合彩中的思考、讨论、选择,能被人们牢牢抓在手心。
悖论的另一部分在于,即使是在其中有所损失,赌民也认为自己能掌握这种“失控”,甚至通过刻意追求这种失控,来让自己获得一种濒死体验,以及对死亡的控制感。在赌民们对“没中奖”的瞬间描述的过程中,这种感受仿佛是人站在悬崖危楼之上,而得知自己没中的那个瞬间,人会回到平地之上,因此虽然没有中特码,却依旧能有在濒死边缘活下来的幸存感。可以说,赌民们热衷将自己放置于危险的边缘,挑战死,是对生的确认。为了消解掉生命之中的矛盾性,生命的激荡、刺激,都需要被消耗掉。投入一场必输的赌博之旅,最终极的目的就是为了输。
隐藏于生命之中的矛盾之力驱使人们活下去:有的人会追求一种受限的自由,或者说自由地受限,主动地让自己沦为奴隶、婴儿和物件;也会追求一种徘徊在死亡边缘的生存状态,一种轻微自毁的倾向——在高楼、水边、马路边行走时,另一侧的深渊往往有致命的吸引力;人在幸福时会感到惘惘的痛苦,在痛苦时又因这痛苦如此熟悉深刻,让自己从庸碌之中脱离出来,感知到神性的幸福。如果没有这些矛盾的对抗,失去了力的牵引与对抗,有些人便难以存活下去。
如今,距离地下六合彩风靡的千禧年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被问起“为什么那么多人明知会输,还一定要买六合彩?”梅芳答,“因为那时候都愚昧啦,都疯。”
我们可以认为,六合彩诞生于对人们的激情和愚昧的利用。但不可否认,它同时也以人们的激情和愚昧为媒介,展现了一个年代的集体无意识。在六合彩这个乡镇冒险中,人们以下注的方式,参与了一种香港梦的神话,用数字、动物、颜色构成的符号充当自己的代理人。在小县城,人们似乎格外容易被激发一种赌徒心态,他们的生活充满了虚拟语气,“如果当初......就好了。”“当时就应该......”。却又因为阶层、资源的限制,导致人们更愿意在熟悉的空间里完成一场表面可控的有安全感的冒险,通过代理机制,用金钱的行动来替代真正的行动。驾驶一艘写着“香港制造”的小船,人们在卧室、堂屋、门廊里出海。唯有赌博,能让人在持续的重复性之中,获得对麻木心灵的一种刺激,也在波澜壮阔的大海中获得一种确定性和掌控感。而这份集体的麻木,在海面倒映出社会的一片荒芜。
(作者:欧椋;编辑:柳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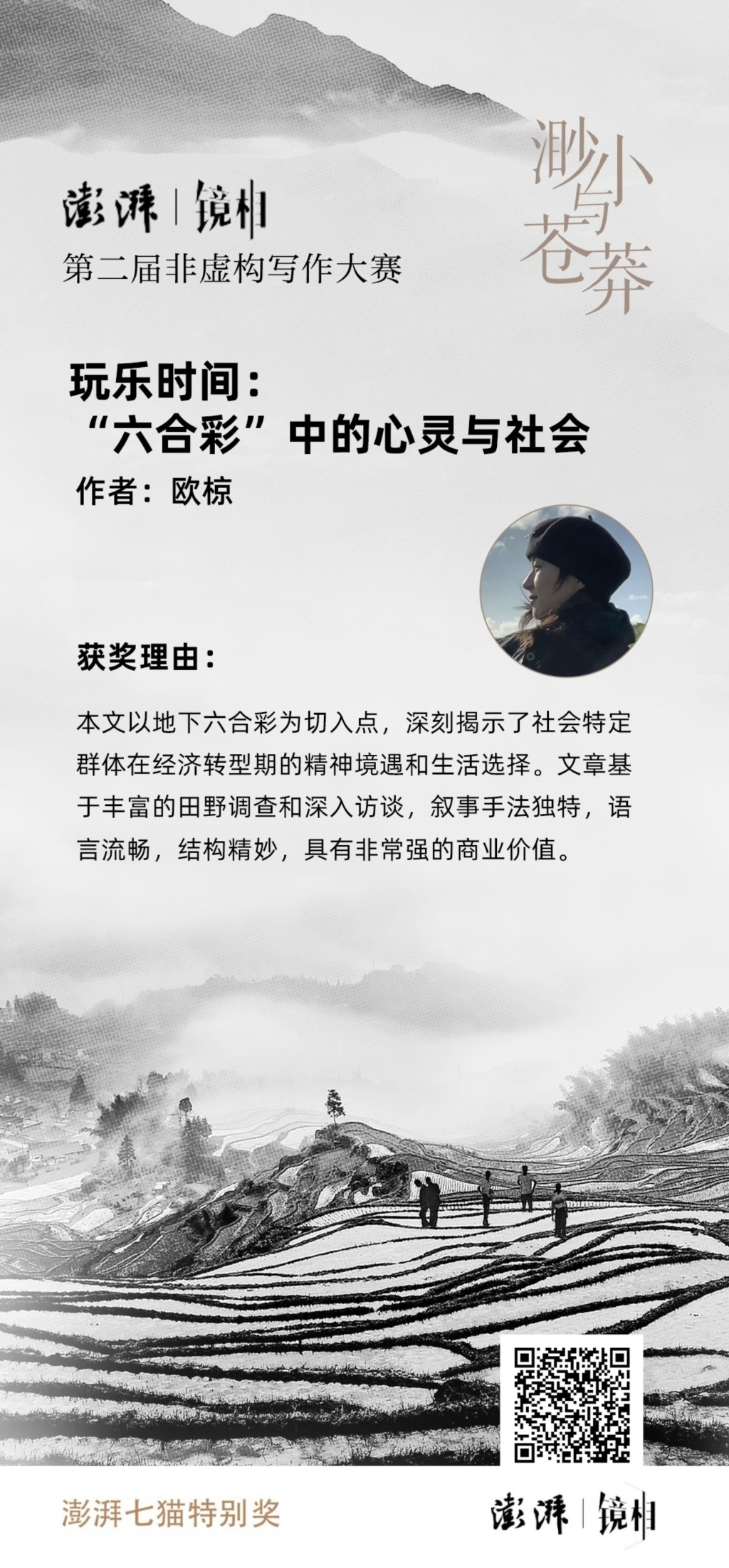
海报设计:王璐瑶
转载请注明来自夏犹清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文标题:《玩乐时间|获奖作品节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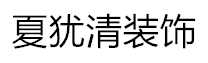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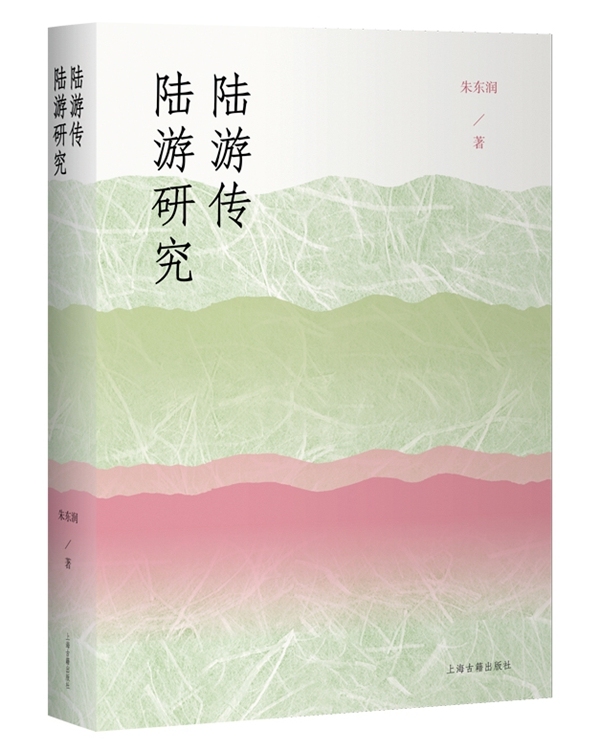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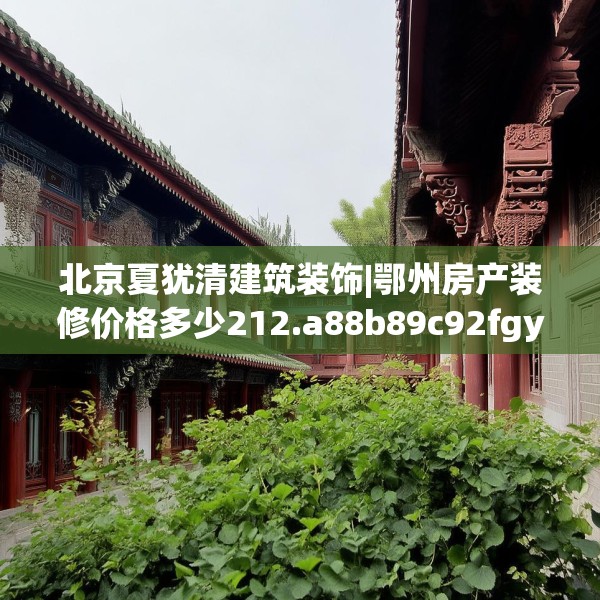



 京ICP备2025104030号-8
京ICP备2025104030号-8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