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华民族在血火淬炼中铸就的永恒丰碑,是中华民族在生死存亡时刻迸发出的磅礴力量,它以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众志成城的团结意志,视死如归的牺牲担当,铸就人民的钢铁洪流,让山河破碎的中国重燃希望之火,引导新中国走上自主、自强、自信的发展道路。抗战精神内化为现代中国的精神血脉,激发了无数经典文艺作品的诞生。新时代以来,文艺创作形式更为多元,人们开始以电子游戏为媒介,重返那段血与火的岁月。电子游戏这一新大众文艺媒介中出现了抗日战争主题,不断打造着新的“中国故事”的主体性叙事范式。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我刊特邀三位学者,系统梳理抗日战争电子游戏从20世纪90年代肇始至今的发展轨迹,总结其类型、特征及价值,并直面其中存在的问题。从真实的战场到虚拟的世界,从血肉之躯的牺牲到像素构建的战斗,游戏让我们以第一人称重返那些艰苦卓绝的岁月。当年轻一代通过游戏走进历史,他们收获的不只是“玩家的胜利”,更是对“人民的胜利”的切身体认。每一次游戏的重启,都是对牺牲者的致敬;每一个关卡的突破,都是对和平的珍视,虚拟的硝烟成为一种独特的纪念方式。理解游戏,研究游戏,因为人们在用这一当代语言缅怀先烈,铭记历史。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的背景下,如何通过数字化媒介实现对抗日战争历史记忆的当代激活,已成为红色文化传承的关键议题。游戏界面提供的情景再现功能,使抗战价值的当下性与游戏叙事的遍历性有机结合。中国游戏从业者基于朴素的爱国热情,自发借用游戏媒介和历史故事创作抗日战争题材作品,形成了从文学故事,到视觉影像,再到游戏机制的三重“文本盗猎”。以游戏《隐形守护者》为切入点,结合重演历史活动的理论框架,可以探讨中国抗战游戏如何通过历史叙事与游戏机制的双向赋能,构建起具有本土特色的历史体验范式。
历史研究中既有关注宏大叙事沿革变迁的部分,也有关注某个特定时代个体命运的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每一个历史事件、每一位革命英雄、每一种革命精神、每一件革命文物,都代表着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取得的重大成就,展现了我们党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汇聚成我们党的红色血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以文物展览、口述史材料、节庆演出、影视作品等多种形式被传承和记录。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作为人们对历史再想象载体的再现历史活动(historical reenactment activities)的形式也在不断更新,人们对历史的具身体验与集体性体验也因此而发生着改变。
一、再现历史活动形态的演进:从文旅到电子游戏
再现历史活动以“发现新的和具有创造性的历史表征模式的能力”极大地影响着大众对历史的认知。历史学者杰罗姆·德·格鲁特(Jerome de Groot)认为,再现历史活动的核心进行方式按照“要旨→事件→影像”(topic→event→image)的规律,不断从触觉中心向视觉中心演进。
“再现历史活动”在中世纪以博物馆、纪念馆和事件地游览为主要方式,其保持着反思型怀旧的特征,更多涉及“过去的不可回溯与人的有限性”。大航海时期(16至18世纪)流行的是历史事件展演(history event performance),包括但不限于舞台剧、音乐剧、节庆仪式等形式。这一时期主要依靠演员“以一种特定叙事规则俯瞰重大事件的故事”的演绎方式,将不同视角下的历史体验遍历(ergodicity)展开。电影被发明之后(19至20世纪),再现历史影像(reenactment history images)成为人们认识历史的主流方式,再现历史影像的前期以电影、纪录片为主,后期则以电视剧和综艺节目为主,战争影像成为再现历史影像的重要组成部分。再现历史活动在用影像塑造视听奇观的同时,也通过再现战争灾难的方式表现历史苦痛性(capital agony),进而实现再现历史活动的教化作用。
20世纪下半叶,再现历史活动迎来了全新的媒介——电子游戏。与之前的三种再现历史活动相比,电子游戏具有独特的知觉具身性:它不再只是强化视觉体验,还通过交互机制将游客/读者/观众变为玩家,并重新赋予受众触觉体验。玩家以操纵游戏角色的方式在界面中完成再现历史的仪式,游戏手柄(键盘、摇杆等)所形成的触觉感受转化为游戏中的“我”(代理行为者)的经历/选择,“我”也最终成为再现历史活动中“虚拟现实的感受主体”,并在数字场景中再度进入虚拟历史。
换言之,电子游戏将原本分离在三种不同再现历史活动中的特性集中到游戏界面上,由此形成全新的个体表征。在电子游戏这种带有明显当下性表征的载体上,在遍历性叙事的结构中,玩家通过“选择”,再度体验了历史关键抉择中的苦痛性,由此“历史性的犹豫时刻被鼠标移动所改变,这一举动似乎恢复了个人能动性,并将历史宏大叙事的缩影变得可以理解”。
二、中国抗日战争电子游戏发展转向
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主题的游戏正是通过游戏演绎中的再现历史活动完成了对玩家历史想象的干预,也就是说,玩家们“沉浸在这些虚拟和戏谑的世界中与过去发生联系,通过积极参与过去的表征,获得了某种历史意识(尽管这种历史意识是扭曲的)”。如载具射击游戏《战争雷霆》(War Thunder,2012)、策略战棋游戏《钢铁雄心4》(Hearts of Iron IV,2016)、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使命召唤:二战》(Call of Duty:WWII,2017)和《荣誉勋章》(Medal of Honor,1999—2012)等,这些优秀的外国游戏作品涉及多种对历史的表现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历史复现”“以史鉴今”“历史游乐场”“历史学者的技艺”。作为书写历史的另一种可能,游戏起到了“历史再现(representation)、历史模拟(simulation),以及改造人类历史”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在数字史学研究上,电子游戏已经成为该学科变革研究的“绝佳线索”。
虽然在外国游戏中,中国的形象大多数时候是中立或正面的,但这些作品并不基于中国主体性进行游戏叙事建构,它们所表现的更多是一种被规训的中国形象,这反而会对中国借由再现历史活动讲述自身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真正价值造成阻碍。正如一句法国谚语所言,“缺席者总是错的”(Les absents ont toujours tort),如果对一段历史的讲述缺少当事方的声音,那么他人为之发出的声音很有可能变成“东方主义视角下强行施加的中国形象,即亟待拯救的中国概念”。故而,在游戏领域不断讲述真正的中国故事,推出属于中国的再现历史活动,就变得尤为重要。
由中国制作的抗日战争题材游戏(以下简称“抗战游戏”),最早可追溯到《地道战》(1996,动作角色扮演游戏)。由于早期《血狮:保卫中国》(1997,即时战略游戏)、《抗日——血战上海滩》(2003,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亮剑Online》(2010,网络角色扮演游戏)等作品的制作水平大大低于玩家预期,导致抗日战争题材逐渐成为游戏企业心目中的“雷区”。但在《隐形守护者》(2019,角色扮演游戏)得到大量玩家好评后,市场仿佛又再度燃起了创作抗战游戏的热情。
2010年代之后,抗日战争题材影视作品主要类型再度从描写正面战场转向敌后战场,而与早期《地道战》《地雷战》等描写敌后游击战场的作品不同,这次转向主要催生的作品类型是“谍战”片,作品主题也从表现战争的宏大场面转向探讨人性在战争中的复杂纠葛。与影视作品的转向相对应的,是抗战游戏作品的类型转向。如2019年在steam上架的抗战游戏——“创新性互动影像作品”《隐形守护者》。抗战游戏向“谍战”题材转型固然有游戏创作者在看到之前的游戏类型市场反响不佳、尝试进行改良的原因,但更重要的缘由是中国的抗战游戏从一开始就高度依赖对影视作品的“文本盗猎”(textual poaching),正是因为有关抗日战争叙事的再现历史影像(reenactment history images)在时代需要与观众喜好下发生了变化,从完全关注前线战争场面逐渐转向关注后方谍战博弈,抗战游戏才随之发生关注重点的转向。
从最早的抗战游戏《地道战》到最新的《谍:惊蛰》(2025,文字冒险游戏),几乎每一部抗战游戏背后都有影视作品作为原型,而且是非常标准的后时性(ultériorité)“盗猎”,不少游戏甚至将影视作品片段作为游戏过场画面,以此标记对该作品的致敬:被“盗猎”文本从《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这样的“老三战”作品,到《暗算》《潜伏》《风筝》《惊蛰》等谍战作品,不一而足。
故而,抗战游戏可以说是“把各种(抗战类型的)节目、电影、书籍、漫画和其他通俗材料连成了一个互文性的网络”,并在再现历史活动中让互文性的网络对历史层叠进行再次“文本盗猎”,最终形成具有历史丰富性(historiocopia)的复杂语境。于是,对于熟悉抗日战争历史和抗战题材影视作品的观众而言,抗战游戏演变为“盗猎的诗意”,游戏制作方在抗战游戏中巧妙加入各种“选择直接映照歌词(历史)意义的图像,不需要语境也可以看出联系”,正因为“这大多数语言-图像的对应来源于观众对(抗战)电视剧叙事的熟悉度”,中国玩家在游戏过程中便更是标记了一份对历史与影像的双重回味。
也正是因为抗战游戏的“文本盗猎”性,让其不仅从游戏机制上,还从叙事机制上再度收敛了再现历史活动在其不同发展时期的三种特性——当下性、遍历性与苦痛性。毕竟,许多原型文本存在的抗日战争历史影像,其本身就包含这些特性。如《潜伏》通过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心理描写展现了当下性,即每个看似孤立的决策都直接影响后续余则成能否继续潜伏的情节;《风声》通过层层递进的悬念设置体现了身处不同阵营人物身份的遍历性,即观众需要不断推理和选择才能理解真相;《伪装者》则通过情感纠葛和角色内心的挣扎展示了苦痛性,即地下工作者不仅需要面对外部威胁,还要应对内心的挣扎。
三、《隐形守护者》的三重“文本盗猎”与“隐形”游戏机制
在抗战游戏谱系中,2019年在steam上架的《隐形守护者》作为集大成者,集合了过往抗战游戏在“文本盗猎”与游戏机制方面的几乎所有特性,在三重“文本盗猎”的叙事数据库中,再现历史活动的三种特性经由“隐形”的游戏机制得到更好的视听语言与玩家交互体验。
(一)相互交织的三重“文本盗猎”
《隐形守护者》继承了抗战游戏的“文本盗猎”特质,游戏的过场画面(cutscene)采用真实的黑白历史记录影像。在此基础上,该作发挥出真实事件、谍战影像与游戏机制的三重“盗猎”,让玩家在以肖途为主角的故事中,通过游戏具身的经历,再现了抗战时期谍战人员所经历的真实历史。
第一重“盗猎”来自对真实事件的历史盗猎。《隐形守护者》的核心叙事围绕主角肖途展开,其原型正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具传奇色彩的“五重间谍”——袁殊。袁殊是中国共产党情报战线的重要人物,他有五重身份:中共地下党员、中统特工、军统特工、日伪政权官员及青洪帮成员。他的经历不仅是《隐形守护者》叙事的核心历史线索,更是游戏对谍战题材深度还原的基础。袁殊的革命生涯始于1931年,时年20岁的他经潘汉年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迅速投身于情报工作。1932年,袁殊以中统特工的身份打入日本驻沪领事馆,成为日本特务机构的核心成员。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巧妙利用多重身份,在敌后情报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充满波折与传奇的人生轨迹,成为《隐形守护者》游戏叙事的现实基础,玩家在虚拟世界中扮演的肖途,正是对袁殊复杂身份与抉择的再现。游戏通过袁殊这一人物原型,将抗日战争时期地下工作者的隐蔽斗争具象化。这种对历史真实性的还原,使《隐形守护者》超越了传统谍战题材的戏剧化叙事,成为一部以历史为根基的沉浸式作品。
第二重“盗猎”来自对谍战片的“文本盗猎”。《隐形守护者》的前身是由玩家范特西(fantasia)制作的独立同人游戏《潜伏之赤途》。与传统谍战题材不同,《潜伏之赤途》摒弃了“二元对立”的叙事逻辑,转而通过多线性选择与道德困境,展现抗日战争时期各方势力的纠葛。该作的创作深受多部经典谍战影视作品的影响,包括《潜伏》《伪装者》《记忆之城》等。这些作品不仅为《潜伏之赤途》提供了历史素材,其视觉风格与叙事手法也都启发了游戏的设计,游戏影像素材原本就是从不同红色影视作品中裁取的立绘。这份亲缘性还体现在《潜伏之赤途》“本身的情节和人物设计就存在诸多致敬谍战题材影视剧的成分”:肖途、庄晓曼、顾君如、李峰等角色在命名方式、人物经历、性格养成等方面都与影视作品呈现强相似性,由此它们共同形成庞大的合并互文性外部世界。通过借鉴影视作品的叙事张力,《潜伏之赤途》成功构建了一个充满悬疑与反转的谍战世界,并为《隐形守护者》的后续发展提供了成熟的叙事模板。
第三重“盗猎”来自对游戏机制的盗猎。《隐形守护者》在还原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通过艺术加工增强了叙事的戏剧性。游戏中对袁殊的五重身份进行了适度简化,将其复杂的政治立场转化为玩家易于理解的剧情线索。同时,游戏通过虚构角色(如武藤纯子、陆望舒)与虚构事件(如肖途与老师孙正清的冲突),填补了历史记录的空白,使叙事更加完整。这种平衡既尊重了历史真实,又满足了游戏的娱乐性需求,使玩家在沉浸式体验中深化了对历史的理解。《隐形守护者》有多达134个结局,游戏第一章里潜伏未开始时,剧终还只是对应肖途到上海站与老师告别后回到边区,在进入第二章之后潜伏失败就直接对应到角色死亡。其中有3个主要的剧情分支方向,分别对应第一主角肖途的不同名字所通往的未来,即以“龟田太郎”的身份赴日结局(扶桑安魂曲)、以“郑途”的身份加入国民党结局(美丽世界、丧钟为谁而鸣)和以“胡蜂”的身份回归党组织的结局(红色芳华)。
除上文提到的外互文性以外,《隐形守护者》的交互游戏机制,让玩家必须站在肖途的视角作出选择,由此产生不同剧情线之间的信息差,进而引发下一步剧情,使其进一步具备强烈的内互文性。不仅如此,《隐形守护者》的文本信息不再是像《潜伏之赤途》那样只靠对话展开(这也是橙光游戏本身的局限),而是随着游戏进程而不断揭开:角色档案里包括日记、事件、报刊、传信等体裁的“隐藏剧情”,通过这些档案之间的相互联系,重现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生存境遇,并构成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对话。
(二)“隐形”游戏机制下的三重特性
《隐形守护者》的游戏机制就是隐形(in-visible),其不仅直指游戏背后的“隐形守护者”主题,同时指游戏中贯穿了多重维度,包括但不限于隐性叙事进程(covert progression)、游戏作者隐身、交互机制隐藏等方式,它们同时存在于游戏的隐形表层(当下性)、隐形中层(遍历性)和隐形深层(苦痛性)中,所形成的复数潜伏结构亟待玩家在游戏过程中不断揭开。
1.隐形表层:叙事画面的当下性
《隐形守护者》的叙事画面完全不同于真人互动电影,也不同于惯常见到的互动游戏,它采用的是静态而非动态、配音而非讲述、当下而非连续的静态图片连续叠加风格,于是被很多玩家戏称为“PPT风格”,尤其是在部分静态画面上还额外追加动画特效,使这种多平面影像的“尖刺感”变得更加明显。玩家在任何时刻按下影像播放的暂停键,都会截到一张不会因为画面运动而产生阴影的图片,这就是静态图片营造的当下性(presentness)。
在整个游戏画面观看过程中,玩家身份重新变为观众。但这时他们已经不再是被动接受本雅明所说的“震惊与分神”的客体可见(visible)观众,而是自主通过“眨眼补帧”图像的主体可视(visual)观众:从主观上说,观众看到的物体(剧情流动与行为)不是闪烁的,而是连续的;但从客观上说,图片视角变化的重新拼贴所达成的额外情动(如第三章“生死途”里庄晓曼与肖途跳舞时,画面就采用了多屏幕拼接的方式),使观众重新意识到静态图片并非只是图片,而是更具多元可能的影像(image)。“影像”作为电影的本体,逐渐代替了以文本为主体的影片(f ilm)而叠化在游戏中,只不过不是横向叠化所形成的过曝,而是纵向叠化所形成的断片。
这也正是“隐形”在视觉层面作为替补方案所带来的“在场的不在场”:虽然整个游戏几乎没有空镜头,但游戏的静态影像创作出无数无时不在的当下性,它们以“时间上的暂停、叙事上的中断、情感上的真空”作为非时序时间(cronos),使肖途在被监控的危险空间中静默下来。于是在当下性的静态影像下,《隐形守护者》的意象世界在游戏机制中被暂时内折(invagination),最后在游戏交互机制的遍历性下,被重新打开,变为更丰富的褶子轮廓(conf iguration du pli),并且在游戏界面上随时都可以查看“不知何时解锁的”角色档案,以及点击位于视听平面之上、一直存在的剧情线/档案按键。
2.隐形中层:交互机制的遍历性
对于历史游戏而言,游戏遍历性在历史演进修辞幻象(rhetorical illusion)下形成游戏叙事与历史事实的混合关系。由此进行的游戏遍历性过程也是历史演进模式的过程,梁亦昆认为游戏文本对应着三种主要的历史演进模式,分别是“线性历史、循环历史以及(伪)或然历史,对应着时间意识上的直线、圆环与分叉”。
三种不同的历史演进模式并非相互排斥,在历史游戏中玩家依然能感受到彼此交互的图示:如果想要打出真/角色/完美结局,必须按照线性历史策略调节好感度区间才能抵达;在游戏过程中不断进入“死胡同”(无论是地图的,还是叙事的),需要依照循环历史策略积累遍历经验/数值才能跳出循环;不同分支剧情的独异性则需要依靠或然历史(伪历史)策略,透过关键选项让角色“在并列世界中移动,使记忆部分地丧失”,产生解离性人格,才能获得更多实践性的历史互动。
在抗战游戏里,遍历性更是为再现历史活动的当代重构提供了多维价值。它首先突破了线性叙事的单一性,通过多线选择与结局交织,立体化地呈现抗日战争时期地下工作的复杂性与历史进程的偶然性。对于玩家而言,正是通过反复体验不同分支,深化了对人物抉择的共情,才使历史记忆从被动灌输转化为主动探索。遍历性同时还将个人命运与集体记忆进行绑定,通过虚拟情境中的“多重人生”,让玩家直观地感受到抗日战争年代隐蔽战线的牺牲精神与信仰力量。
在《隐形守护者》中,这种遍历性主要体现在作为剧情探索的显性“历险”、作为知觉体验的隐形“历程”与作为视听共鸣的隐形“历经”上。“历险”的结局对应剧情,“历程”的路线对应知觉,“历经”的回声对应视听。“历险”是可见、可抵达的显性文本,正是在“历险”分支各项信息剧情弥合的前提下,玩家也就忽略了是“历程”与“历经”在游戏机制中以幽灵形态(隐形),调动着对抗日战争时期真正历史叙事的情感共鸣。
其一,“历险”的结局。“历险”在于诸多选择分支必须遍历之后,玩家才能对单一情节线上的角色命运选择获得更加深刻的理解,其中,不同结局的内容互文与结局先后达成的顺序,都会影响玩家对该游戏的首次情动体验。
如果玩家一开始就无法相信“历险”所塑造的隐形潜伏,在游戏序章就可能达成“上海站”结局。其中作为首个不用回溯失败的“好梦还乡”结局,不仅有“剧终”字样,还有对肖途一生简单的概括——“回到边区后,投身大后方建设,成为乡村语文老师,献身基层教育事业”。在第六章“至暗抉择”中,当肖途在面对“第二号”的“你是否愿意继续这种忍辱负重的人生”时选择“我太累了”会达成最后一个“剧终”字样的“平凡世界”结局。在经历诸多“历险”之后,肖途在潜伏中不断读档/存档之后活到信息量最长的“红色芳华”结局,同样有“全剧终”字样。这次是用画面(而非文字)展现出肖途的暮年:他在苏北芦芝乡(边区)成为一名乡村语文教师。这三个结局之间的游戏信息含量是整个游戏中差别最大的,同时也是100余个结局中最接近的。虽然故事最后还是回到了起点,但在循环历史的“历险”中才具备互文性的意蕴。

《隐形守护者》中主人公经历诸多 “历险” 之后的 “红色芳华” 结局。
不过,如果肖途真的选择了“好梦还乡”,只有遍历所有剧情线的玩家,才能猜到在这条世界线下的其他角色的经历会怎样,几乎可以说在没有肖途参与并且改变诸多人物历史轨迹的情况下,方汉州、方敏、庄晓曼、顾君如、陆望舒、董旺成等人都会死于非命。问题也正在于此,玩家将如何尽可能“历险”所有剧情,甚至能遍历三大结局?《隐形守护者》不是可以自主选择的“并列世界”游戏,而是需要遍历所有可能主线的历史游戏,所以游戏在选项上进行了先后可能性引导。
重点在第五章“菊·刀”,“菊”代表“扶桑安魂曲”线,“刀”代表“丛林法则”线(后续分支为美丽世界/丧钟为谁而鸣结局),而其中的隔点(“·”)作为未言明的内容,代表着“红色芳华”线。第五章关键剧情有两处:一是章节开始时需要选择是否去见浅野,此处并没有标记“这是一个影响深远的选项,请谨慎选择!”(以下简称“深远标记”),一旦选择见浅野,就无法开启“红色芳华”线;二是在章节中段,需要选择是否刺杀浅野,此处出现“深远标记”,更容易导向“丛林法则”线。“菊.刀”也是唯一带有“标点”的章节标题,它居于游戏章节的中位线,向我们揭示了游戏的三种可能结局,同时也是“火车车厢”衔接的象征符号。在第六章“至暗抉择”中肖途还需选择下车找接头人/留在车上,此处依然没有“深远标记”,却也是开启“红色芳华”线的关键选择。于是,在看似游戏作者退场,并交付玩家自由选择的“隐形”下,玩家更容易被诱导进行“扶桑安魂曲—丛林法则—红色芳华”线的先后遍历,这正是游戏制作者有意设计(intentionally designed)之下意图达成的情感经历。

《隐形守护者》第五章开始出现的重要 “分支路线”。
除了“历险”信息的完整性对比,在玩家的主动作用下,“历程”顺序的先后差异所获取的信息,也会带给玩家完全不同的知觉:按照作者优先暗示的选择剧情通关的玩家,会对肖途产生革命信仰越发饱满的共情感;而先完成“红色芳华”线,后通关其他结局的玩家,则会对肖途的作为产生强烈的苦痛耻感,因为他原本可以不用步入这样的结局。
其二,“历程”的路线。“历程”作为开启/关闭并列世界之间跳转的方式,它原本就可以脱离剧情线,而以形式本身调动玩家的情动体验。“历程路线”不只是上文所说的先后顺序(对玩家不可见)与并列世界(对玩家可见,对肖途不可见),在《隐形守护者》中我们还能看到更多着墨于历程、刻意隐形/显形交替进行的方式,并通过这些方式象征着潜伏者在历史现实中的不同选择。
游戏过程中玩家会遇到数次“这是一个影响深远的选项,请谨慎选择!”的提示,这些选项并不会立刻改变游戏过程,而是会在故事后期对剧情走向产生重要影响。与之相似的还有“有人记住了你的回答”(以下简称“记住回答”)的提示,其作用是通过提供一种或然历史的“分叉”历程进行一种玩法上的“隐喻”。“记住回答”的提示隐喻着潜伏工作者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处在一种“隔墙有耳”的危险中,围绕在玩家身边的危险通常来自特工庄晓曼这个角色的行动,而更巨大的危险则来自暗潮汹涌的潜伏环境。
在诸多结局中,除了剧终、潜伏失败(即死)和终章以外,还有一种隐形结局,那就是“循环结局”,即因为某块前置剧情缺失,导致无论作出怎样的选择都无法开启新的剧情线(即无法通关),这就是“深远标记”的第二个功能:一旦“深远标记”未被选中,之后抵达下一章的剧情线就会被永久性关闭,虽然现实世界的时间不是周期循环的,但肖途只能处在“无始无终的轮回之中”作为没有出路(sans issue)的在场。
当故事进入终章,虽然玩家还可以进行选择,但所有选项都不再具有分支性,而是可以遵从本心进行。历程路线的第四种方式直至最后才出现,那就是“线性选项”。肖途的对话不再具有选择功能,其机制也从多线性叙事游戏转为视觉小说,交互本身也变成了“一条单向的、不可逆的目的论式的时间轴”,制作方即“作者隐匿于文本背后的强大控制力和情感力”开始走上“舞台”。
由此,数字游戏历史书写的三种演进模式:“直线(线性选项)、圆环(深远标记、黄色字体)和分叉(深远标记、记住回答)”,被重新嵌入《隐形守护者》之中。
其三,“历经”的回声。“历经”的回声不只是业已发生的历史事件中人物原型和事件与游戏中的相似性比较(增删),同时也是(伪)或然历史用以安放玩家/角色(肖途)重走潜伏之路的可能。
对于肖途来说,在没有上帝视角的情况下,死亡几乎是必然会到来的事,不仅因为“历程”干扰了游戏内的选择,而且因为这是历史游戏所观照到的真实历史的过往:那些死亡结局,对于参与真实斗争历史的地下潜伏者而言,已经历过无数次,这又何尝不是一种遍历性,只不过不是某一个人的所有可能遍历,而是所有人对某一目标的所有可能遍历。
“历经”的回声最容易出现的地方,同时也是《隐形守护者》游戏出现差评的第一波浪潮时:在第十章“极恶非道”里,肖途要通过聆听不断倍数扩展的“滴、滴滴、滴滴滴滴”回声,并按照相同的逻辑旋转瓶子,以解救武藤纯子。要说哪种“历程路线”更能让玩家有代入感,那便是“倒计时选项”,它的出现正是把“滴滴”幻声可见化,即从听觉上观看(audioviewing),如果说“滴滴”的快速听觉标点(auditory punctuation)所定位的时刻变成一阵阵弹道痕迹,那么不断减少的数字就是生命可能丧失的倒计时。而在这个选项前后,玩家会明显感觉到游戏中甚少出现的过肩镜头:即肖途的后侧成为画面前景,刺杀他的枪手前侧位于画面中间。这样的视觉出发点是肖途,而视觉重点就是枪击者。这让《隐形守护者》短暂地成为视角游戏(point of view games),并通过亲历性而非遍历性营造出可视化“历经”体验。过肩镜头还出现在另一个角色身上,那就是已经变成国民党高官秘书/“第三号”的方敏,游戏作者通过她与“第二号”对话的镜头语言,揭示了方敏就是另一个未被游戏玩家见到/玩到的、却在“历经”中存在的隐形守护者。
方敏的作用还不止于此。如果我们从媒介载体化身来看,完成“历经”记录者的其实就是肖途所遇到的四位女性,她们分别代表书本、记录、档案与见证,当其中任一女性没能活到最后,也就意味着肖途作为被记录主体的消匿:武藤纯子写下了回忆录《时代的虚言》,这本书可以认为是她以“自己所知道的肖途”为基准讲述的不可靠叙事;方敏做了一份肖途的党员证明材料,采用模仿字迹的方式完成一份“虚假”的档案记录;从履历来看,庄晓曼更像胡蜂,如果我们只看每章最后的档案记录,就会发现庄晓曼有可能出现在肖途所在的任何任务中;陆望舒则以“假戏真做”的方式,陪伴了肖途的后半生,她自己就是隐秘的见证者。
3.隐形深层:历史游戏的苦痛性
无论是哪一个游戏结局,肖途都会面临强烈的苦痛性:虽然他自己不会遍历玩家的无数个即死结局,但无论是哪条结局线上的他,都无法摆脱失去身份所带来的自我丧失感。对于大部分游戏来说,苦痛变体有两种:“肉体上的自我毁灭”(即角色死亡)的物理痛苦;“主人公活了下来,却为自己造成的痛苦而感到内疚”的心理上的痛苦,肖途在游戏中的虚构悲剧就属于后者。
这份心理苦痛就是“非死的主体性”:尽管“机会的丧失”会阻绝情感共鸣,读取存档会“对平行的可能世界的不断筛选和删除”,但肖途同步失去的并不只是作为游戏角色的生命,而是身份证明。在整个游戏里,肖途多次失去自己的身份,能够证明自己身份的档案/上线/同伴/情报/领导都先后离他而去。在这一过程中他的信仰也开始逐渐被撕裂,当不可见的差异变成可见的抉择时,真正的剧情支线才得以出现,于是他的新名字(胡蜂/龟田太郎/郑途/肖漆仁)成为掩盖心理苦痛的新档案。直到“红色芳华”线最后,肖途才最终找回了自己当初返回上海时的情动——那份属于自己、属于档案、属于历史、也属于死亡的“大写的历史”,同时那也是大电影(archicinéma)的大苦痛(capital agony)。
这份大苦痛在《隐形守护者》中至少以双重面相绵延于游戏过程中,姜宇辉对阿基·贾维南(Aki Järvinen)关于这份苦痛的来源与区分的阐释做了进一步细化:“一是日常(mundane)之痛,比如耻感和罪感;二是生存(existential)之痛,最根本的正是死亡之惧 (fears of death)……日常之痛显然源自具体的对象,而生存之痛则源自不确定的氛围和事件。”肖途的日常之痛所对应的具体对象不仅是每章节的“死刑执行官”,同时更是隐喻性空间。傅善超认为,《潜伏之赤途》缺少的正是这种隐喻性空间,因其图像小说的类型,导致主角方别没有日常生活,当然也没有自己的立绘。而他所面对的其他角色,其姓名与立绘因为素材来自同人互文,这令玩家在游戏过程中产生强烈的代入感分裂。肖途的生存之痛就是死亡否定本身。玩家的代入(游戏反复死亡)与肖途的代入(在正确的路线一直生活)在并列世界的反复切换中形成双层“代入裂隙”;角色身体在静态图片的刻意悬置下变得缺少能够直接感知到流血与死亡的痛感,则成为第三层“代入裂隙”结构。
不过,《隐形守护者》作为历史游戏与现实题材游戏的兼名,正是将再现历史活动(肖途的生与诸多地下工作者的死)作为解决“代入裂隙”的生成结构:它通过打造事件地图的方式,完成了正统历史无法再现的确有其事的真实感。肖途作为“具有历史主义意识的表演者”,我们可以认为他同时也是另一个玩家,无论他的指认对象是原作方,还是原型袁殊,都是对过往抗日战争十余年里那隐形历史的再现——所以他既是(玩家操作的)客体,也是(共有历史再现的)主体。
在这个层面上,就如肖途日常之痛的编织作用一般,肖途的死亡之痛也能产生同样的作用,他在自己剧情线中的“虽生犹死之痛”和玩家在并列世界中的“虽死犹生之痛”交织起来,让虚构故事与真情共鸣,旁观身份与情动代入同处于游戏时刻,这也是“为了回溯死亡、感知死亡,感知与死亡相关的一切深刻情感而存在的叙事”。
余论
《隐形守护者》等抗战游戏作品通过“历史盗猎-文本互文-机制创新”的路径,突破传统红色叙事的单向传播模式,以互动性、情感化的设计激活玩家对抗日战争历史的主动共情,活化了玩家的红色记忆。但我们依然需要认识到,中国的游戏研究对再现历史活动的理论适配还处在起步阶段,无论是游戏开发者还是玩家,对历史游戏如何体现历史叙事的认知大多还停留在视觉奇观与剧情反转层面上。
这种困境既源于中国游戏产业早期重商业轻文化的发展惯性,如抗战游戏长期依赖对影视文本的“盗猎”,技术发展滞后于叙事需求,也与学术领域对游戏作为历史载体的跨学科研究不足相关。《隐形守护者》的宣传标语为“创新性互动影像作品”,游戏素材的拍摄制作过程都按照真人演员的拍摄方式进行,但该作依然是非常标准的多线性叙事游戏,游戏中以定格影像作为视听语言的呈现方式,尽管制作方将其称为“有声图片剧”,但放之于2025年也很难再说其有足够的技术创新。
突破这一局面的关键,在于构建兼具历史纵深与游戏本体意识的研究范式。另外,还要推动抗战游戏从本土叙事向全球对话的升级,既要警惕西方视角对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的误读,也应通过多视角叙事展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协作。唯有如此,抗战游戏才能超越娱乐产品的范畴,成为兼具学术价值与文化传播力的数字历史容器,在再现历史的过程中完成对民族记忆书写方式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本文系2025年度山西省青少年发展研究课题“美育视角下电子游戏对青少年的审美影响研究”(项目批准号:QSNFZ25157)阶段性成果。】
转载请注明来自夏犹清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文标题:《抗日战争电子游戏的情感叙事转向——以《隐形守护者》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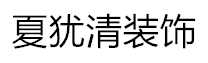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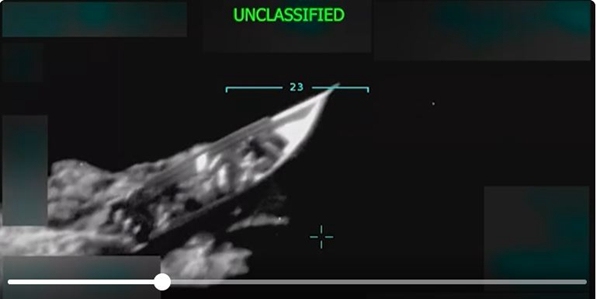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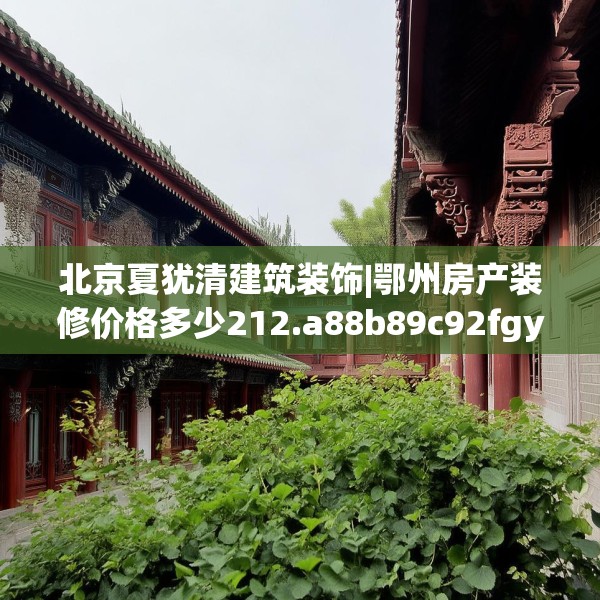



 京ICP备2025104030号-8
京ICP备2025104030号-8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